作者:{admin 整理}
作者:周 浩 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深入发展,以网络为媒介,面向不特定人实施的网络诈骗案件,层出不穷,花样翻新,成为侵财类案件的“重灾区”。
网络诈骗犯罪,因为信息蔓延性、网络技术性和人身非接触性,法律问题争论比较多。具体来看,主要是集中于四个方面:
第一,相比于普通诈骗,电信诈骗较为严苛,犯罪数额采取最低标准,证据规则相对弱化。但是,电信诈骗内涵外延较为模糊,怎么界分电信诈骗与普通诈骗,是个问题。
第二,网络诈骗犯罪,通常由犯罪团伙完成,有严密的组织和分工。不同层级的团伙成员,是主犯,还是从犯,往往存在争议。
第三,认定犯罪数额,是侵财类犯罪面临的主要问题。鉴于网络的非接触性和技术性,电信网络诈骗案,犯罪数额的认定,变得更加复杂。
第四,网络诈骗案件,是此罪还是彼罪,比如说诈骗罪与非法经营罪,诈骗罪与开设赌场罪,司法认定常常存在分歧。同案不同判的情形,不在少数。
站在刑事辩护的角度,我们要深刻把握此类案件的问题,从多个方面为当事人争取有利局面。
1
网络诈骗与电信诈骗
2016年12月,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出台《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电信诈骗意见》),目的在于有效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
相较于普通诈骗案件,《电信诈骗意见》有三点内容明显不同:
首先,追诉标准全国无地域差别,实行统一标准,“利用电信网络技术手段实施诈骗,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
其次,未达到相应数额标准,但接近的,会被认定为“严重情节”、“特别严重情节”。“接近”,一般应掌握在相应数额标准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再次,相对减轻控方证明责任,可以不用逐一收集被害人陈述,综合认定犯罪数额,“确因被害人人数众多等客观条件的限制,无法逐一收集被害人陈述的,可以结合证据,综合认定被害人人数及诈骗资金数额等犯罪事实”。
可见,就《电信诈骗意见》规定来看,成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数额标准要求低,证据规则相对弱化。为此,准确界定电信诈骗和网络诈骗,避免普通诈骗案件适用《电信诈骗意见》,将会对当事人产生重要影响。
关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内涵外延,《电信诈骗意见》未作出明确规定,相对较为模糊。最高检出台的《检察机关办理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指引》,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进一步规定为: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电话、短信、互联网等电信网络技术手段,虚构事实,设置骗局,实施远程、非接触式诈骗,骗取公私财物的犯罪行为”。
结合上述规定以及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定位和社会危害性,电信网络诈骗罪的认定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
一是,面向不特定多数人;二是,采用远程、非接触式方式诈骗;三是,采用电信网络技术手段,诈骗信息具有蔓延性。
尚未具备三个条件,如面向的不是多数人,就不是电信诈骗。
例如,李某诈骗案,“尽管被告人利用了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也客观上使被害人基于对第三方支付平台和网上银行转账信息的信赖产生错误认识,先后被骗7次,但是其诈骗对象仅针对被害人李某某一人,也不存在首先通过网络向不特定多数人发布虚假信息,而最终只有1人予以回应被骗钱财的情形。
因此,该笔20935元指控应依法认定为普通诈骗,而非电信网络诈骗。((2017)鲁0305刑初321号刑事判决书)
不是面向不特定人诈骗的,也不是电信诈骗。比如徐某某诈骗案,“被害人除了张某,其余被害人均是以前找被告人徐某某办理过分期购买手机的客户,被告人是有预谋的利用自己原来给客户服务过的身份挑选还剩余分期贷款没有还清的客户作为犯罪对象。
虽然被告人徐某某获取财物时采用了网络技术手段,但并非是面向不特定的大众实施诈骗,不宜认定为电信诈骗”。(参见(2018)粤0306刑初1230号刑事判决书)
采用面对面、接触方式诈骗的,通常不符合“非接触式诈骗”,不宜认定为电信诈骗犯罪。但是,具体则要进一步判断诈骗方式是否有足够的、充分的接触,还是说双方接触只是为了获取财物。
总之,采用网络技术手段的诈骗案件,未必都是电信诈骗案件。准确界定电信诈骗案件,避免将电信诈骗案件的规定适用于普通诈骗案件,有助于精准辩护,保障当事人权益。
2
主犯、从犯的认定
网络诈骗的实施,基本可以覆盖话术培训、业务办理、日常管理、拨打电话、发送短信、假冒身份、汇款取款等等行为过程,多有组织、策划、部门分工、各司其责、成员众多的情况。
《刑法》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规定,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电信诈骗意见》规定,多人共同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对其参与期间该诈骗团伙实施的全部诈骗行为承担责任。在其所参与的犯罪环节中起主要作用的,可以认定为主犯;起次要作用的,可以认定为从犯。
区分共同犯罪主、从犯,关键是判断行为人是不是犯意发起者、犯罪纠集者、指挥者、主要责任者,是否参与犯罪的全过程或关键环节等方面。
第一,受雇佣、被管理的情形
网络诈骗团伙性、组织性较强,判断行为人是不是团伙核心成员,就成为主、从犯认定的关键。有的团伙型、平台型电信诈骗案,行为人虽具体参与、实施电信诈骗活动,但不是诈骗活动的发起人、组织、策划者,不是核心成员,只是接受公司派遣、安排,未就团伙诈骗共谋的,一般不宜认定为主犯。
例如,在某平台诈骗案件中,行为人按照诈骗金额提成领取工资,接受平台的指示从事诈骗活动。此类人员就公司策划的诈骗活动,服从剧本,分工明确、密切配合,形成完整的犯罪链条。就链条上的人员来看,均由核心成员招募而来,受制于团伙核心人员的管理和制约,彼此相对独立,分工明确。根据团伙中的地位、分工、作用,此类人员不宜认定为主犯。(参见(2014)浦刑初字第5287号刑事判决书)
第二,核心成员不在案的情形
网络诈骗窝点性、境外性色彩明显,判断行为人是不是主犯,不能只在已到案的人员之间相互比较,而是要放在整个网络诈骗案件中全面的看。
因为有的行为人只是在到案人员之中作用明显较大,收益较多,管理职责较高,但是在整个网络诈骗组织中,特别是与那些未到案的核心人员相比较,依旧只是领取工资报酬,受制于他人管理和分配的小角色,而非窝点的负责人,管理者。
行为人的作用,相较于更低层级的人员起到较为主要的作用,但是相对于平台出资方、搭建方、策划方而言,作用仍然较为次要,可以认定为从犯。
例如,陈某指导田某等二人,在诈骗犯罪中的作用明显大于后者,但在整个犯罪过程中,三人皆为招录进来,受袁某等人节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和地位是辅助的。作用低于袁某等人,应为从犯。(参见(2019)浙068刑初45号刑事判决书)
网络诈骗案中,主、从犯的认定,组织、策划、发起,相对易于辨别。只是诈骗环节上的其他人员,大多是通过网上招聘或同乡、朋友介绍等等参与团伙诈骗的,是主犯还是从犯,需要认真把握。
3
犯罪数额的认定
网络诈骗犯罪,作为侵财类案件,量刑轻重严重依赖犯罪数额的多少。因此,围绕犯罪数额展开辩护,是网络诈骗案件的常态。
第一,扣除非参与期间的犯罪数额
《电信诈骗意见》规定,多人共同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对其参与期间该诈骗团伙实施的全部诈骗行为承担责任。
浙江地区《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规定,普通业务组长,以其参与期间主管的小组成员诈骗数额总额认定,量刑时参考具体犯罪时间和作用。普通业务员,原则上认定为从犯并以个人参与的诈骗数额作为量刑依据,同时参考其具体犯罪时间和收入。
根据以上规定,行为人对于非参与期间的数额不承担责任。要注意区分的是,普通业务员和业务经理负责的范围不同,普通业务员仅对自己实施行为负责,即限于自己诈骗的被害人。
例如,匡某甲团伙有明确分工,各人负责自己的区域,各键盘手仅对自己诈骗的被害人负责,不对全案承担责任。本案被不起诉人李某某仅对自己诈骗成功的四名被害人的2050元承担刑事责任。根据两高关于电信诈骗的司法解释,被不起诉人李某某的犯罪金额尚达不到构罪标准。(参见衡祁检公诉刑不诉(2019)113号不起诉决定书)
第二,扣除事实不清的犯罪数额
网络诈骗案件,认定犯罪数额更多的是依靠书证、电子证据等进行综合认定。在案证据不能认定的情况下,就会存在部分数额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面对网络诈骗案件,可以重点把握两个方面:
一是,要重视证据的关联性,即证据能否将受害人的损失与团伙、与个别人员具体的联系起来。比如说,在案证据不能将受害人与被告人关联起来,这部分数额就会被扣除。
最高检第67号指导性案例就曾特别提到这个问题,要关注被害人与诈骗犯罪组织间关联性证据调取的完整性。
围绕证据的关联性,检察院要求公安机关补充调取犯罪嫌疑人使用网络电话与被害人通话的记录、被害人向犯罪嫌疑人指定银行账户转账汇款的记录、犯罪嫌疑人的收款账户交易明细等证据,以准确认定本案被害人。(参见检例第67号张某等52人电信网络诈骗案)
二是,要分析犯罪数额中有无存疑的数额,即哪些数额不能被证据证实。
例如,在淘宝刷单类诈骗案件中,为进一步骗取被害人的信任,吸引更多被害人“刷单”付款,行为人对被害人有过退款操作。
因此,退款记录就成为本案犯罪数额必须扣除的事项,对于其中无法确认是否为退款的几笔,因无法排除合理怀疑,按照有利于被告人原则视为退款。(参见(2015)杭余刑初字第1235号刑事判决书)
犯罪数额的多寡,直接影响量刑轻重,尤其是会影响量刑档次的升高与降低。因此,犯罪数额辩护方面,应通过在案证据尽力辩驳,确保有问题的、有疑问的数额不被认定。
4
此罪与彼罪
同诈骗罪相比,非法经营罪和开设赌场罪,定罪条件和量刑明显轻缓。适时转向其他犯罪,探讨此罪与彼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辩护方法。
第一,非法期货类案件,诈骗与非法经营
借助网络媒介,期货交易愈发便捷。与之相关联的违法犯罪活动,如诈骗案和非法经营案更是层出不穷。
《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六条规定,“未经国务院批准或者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设立期货交易场所或者以任何形式组织期货交易及其相关活动”。
不具备期货交易资质的平台开展期货类业务,被认定为非法经营行为,是期货类案件法律适用的兜底条款。需要指出的是,期货类犯罪行为,是诈骗,还是非法经营,关键在于审核交易平台的虚假性和经营行为的对价性。
进场交易时,客户建立仓单,限于入金、出金、手数,无法对交易的其他参数进行选择。交易平台与国内国际市场行情相连接,资金具有流动性,平台不能通过后台篡改数据、制造亏损的,不宜认定为诈骗罪。
特别是,在案证据如不能证实期货类交易平台被操纵、调控走势,虚构数据的情形,不应认定为诈骗罪。
例如,“不能证明被告人通过控制行情的涨跌或交易对手,在交易过程中操纵价格等事实,现有证据尚不能充分证明构成诈骗罪。洪某某等人是以进行现货交易为名,行组织期货交易之实,应定性为非法经营行为“。(参见(2019)苏02刑终125号刑事裁定书)
第二,网络赌博类案件,诈骗与赌博
网络类犯罪多种多样,准确认定相关罪名,才能做到罪刑均衡。是赌博罪、开设赌场罪还是诈骗罪,对被告人而言,量刑较为悬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设置圈套诱骗他人参赌又向索还钱财的受骗者施以暴力或暴力威胁的行为应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 》曾提到过,“行为人设置圈套诱骗他人参赌获取钱财,属赌博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以赌博罪定罪处罚”。
可见,赌博同样会带有诱骗的色彩。但是,赌博与诈骗有根本区别,即赌博性质上是射幸行为,结果具有偶然性。
赌博、开设赌场,设定的是赌博规则,参赌人员赢输不确定。网络诈骗则相反,是借助赌博的外壳,通过平台操纵投注结果,或是直接控制场内资金的方式非法占有他人财物。
因此,判别二者的关键:
一是,要看赌博平台能否控制投注,有无外挂作弊软件,参赌人员输赢是否确定;
二是,要看行为人是营利目的还是非法占有目的;
三是,要看赌博网站是否虚假,参赌人员能否控制资金投注;四是,要看平台与参赌人员赢输比例。
例如,“以营利为目的,通过邀请人员加入微信群的方式招揽赌客,根据竞猜游戏网站的开奖结果等方式进行赌博,设定赌博规则,利用微信群进行控制管理,在一段时间内持续组织网络赌博活动的,属于开设赌场“。(参见指导案例106号谢检军开设赌场案)
综上所述,网络诈骗案件面临的疑难或争议问题较多,司法认定具有多样性。作为辩护人,我们可以从问题意识入手,结合具体案件提出有益的方案,实现辩护的有效性。
投稿转载说明投稿邮箱:543183107@qq.com |
本帖子中包含更多资源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账号?立即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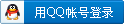
x
|